实施到位
民航第一轮体制改革,比原定时间推迟了一年。1980年3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航总局不再由空军代管的通知》,明确除航行管制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执行外,其他工作均向国务院请示报告。随后,国务院发文确定了相关具体事项,包括终止义务工役制。民航总局的机构编制,由原来参照军队按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工程部设置,改为按政府部门的司局序列设置。
军民航发展关联度很高,民航在很多方面需要部队支持。新中国成立之初,成立了军委民航局,后来较长时间在相关方面归军队领导。“文革”期间则完全纳入军队建制。这在当时国家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对保持行业稳定和正常运转,起到了重要作用。实行义务工役制保证了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对文化程度也有一定要求。但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原有体制就不合时宜了。要通过改革,实行军政分管,按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走企业化道路,才能促进民航业的发展。
《邓小平年谱》在1980年有一段记述:“2月14日,听取沈图对民航工作的汇报。指出:民航一定要企业化,这个方针已经定了。民航总局归国务院直接领导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值得注意,这是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改革文件下达之前所讲的话。结合前面改革推迟的变化,更能体会他对民航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记得当时为配合民航的改革,《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民航要走企业化的道路》。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之下,这步改革顺利完成。
第二轮重大改革
政企分开增活力
民航的第二轮重大改革,是实行政企分开,航空公司、机场和服务保障系统分设。从1984年酝酿至1992年基本完成,持续8年。这期间,我先在民航局政策研究室工作,后到计划司任职,对这次改革比较了解,承担了相关工作。
精心谋划
我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城市的改革,也就是全面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的。民航的改革可谓是紧锣密鼓。在第一轮军政分管、实行企业化的改革基本就绪以后,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就精心谋划新一轮重大改革,从提出酝酿到确定方案,大约用了3年时间。
1984年8月底~9月初,民航局党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讨论了体制改革问题,会后向国务院报送了改革意见。10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题研究民航发展和体制改革问题,民航局局长沈图同志作了汇报。会议确定了民航体制改革的方针原则和支持民航发展的重大政策。1985年1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民航局《关于民航系统管理体制改革的报告》。3月上中旬召开的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体制改革是一个重要议题。
在此期间,李鹏副总理在国务院主管工交工作,对民航发展高度重视。他出席1985年3月的民航工作会议,作了重要讲话。会后民航局主要领导新老交替,胡逸洲同志任局长。这一年先在民航局机关层面进行了准备。1986年上半年对下属单位进行调查研究。
据《李鹏经济日记》记载,他于1986年7月8日、7月12日、7月16日、8月17日,连续4次召集研究民航体制改革问题,听取民航局的汇报。8月17日的日记记录了所确定的三项原则:“(一)政企分开。(二)力量不过于分散。(三)保持竞争。”11月13日,李鹏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民航工作办公会议,研究同意民航系统改革方案和实施步骤,1987年1月国务院正式行文批准。
“国务院民航工作办公会议”是李鹏同志于1985年提议设立的,是针对当时民航发展很快,改革处于关键阶段,安全压力很大,需要加强领导,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李鹏同志非常深入务实,对重大问题抓住不放,他任副总理、代总理、总理期间,为民航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
稳步实施
胡逸洲局长紧握民航改革发展的接力棒,带领民航局领导班子,组织实施了全行业的第二轮重大改革。国务院批准民航局的改革报告后,他从1986年4月17日起,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原民航成都管理局进行试点,目的是调查论证在政企分开、航空公司与机场等分设中,职能、业务、人员、资产如何合理配置。这个工作组有体改办主任、组织部长和相关司局的几位处长。我作为主持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副主任,参加了部分工作。但在工作进行了半个月的时间,胡逸洲局长因回京处理华航机长驾机飞抵大陆要求定居事件,试点工作没有进行完毕,但仍有部分同志留下,继续摸清情况,商讨具体划分办法。
在李鹏同志召集反复研究、国务院正式批准改革实施方案后,民航局确定在上年工作的基础上,仍在西南地区先行改革。1987年10月15日,中国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成都双流机场宣布成立。当年12月进行了华东地区民航的改革。1988年~1990年相继完成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民航的改革。1991年和1992年分步实施了中南地区民航改革。至此,民航新型管理体制架构基本形成。从起初谋划算起,经历了沈图、胡逸洲、蒋祝平三任局长。
李鹏同志组织反复研究改革实施方案,其中一个焦点,是成立几个航空公司为宜。民航局报告并经中央原则同意的,是以原来6个地区管理局为基础,组建6个公司。但到正式实施时,对此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成立两个或三个公司。经过反复论证,仍然维持成立6个公司。应该看到,虽然后来又进行了重组,但在当时情况下,就地组建公司有利于平稳过渡,保持安全运行。至于为什么选择西南地区试点和先改,后来在与胡逸洲老局长一次交谈中,他说主要是考虑华北、华东、中南业务更忙,西北和东北规模又相对较小,而西南处在中间水平,生产运行压力小些,又比较具有代表性。老一辈倾注的心血说明,看事容易做事难,主要领导肩上的担子最重!
放开搞活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的活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不再作为政府的附属物,而成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随着民航航空公司和机场的组建,扩大了经营自主权,增强了内生动力和市场压力,从而大力改善经营管理,促进了航空运输业务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
民航实行政企分开,所包含的意义,也是要放开市场,依靠各方面力量,发展民航事业。政企分开,政府转变职能,就意味着政府部门要面向社会,支持市场主体的兴建和发展。根据民航专业性较强的特点,当时坚持中央和地方合资经营航空运输企业。1984年和1985年,民航局与福建、新疆、云南等省区联合成立了航空公司。在那一阶段还成立了上海、武汉、四川等航空公司。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掀起新一轮开办公司的热潮,海航、深航、山东航均在那一阶段成立。这些企业的兴办,增加了新生力量,强化了市场竞争,促进了行业发展。
在实施改革中,国家对民航相继采取扶持政策。从起初的利润和外汇收入“一九分成”,到后来设立“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以及推行运价体制改革,都起了重要作用。拓展融资租赁,保证了运力增加。在机场建设方面寻求利用软贷款,中央和地方联合投资,并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众人拾柴火焰高,改革迸发新动能,整个行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第三轮重大改革
重组开辟新天地
民航第三轮重大改革,是实施企业重组,与民航行业管理部门脱钩;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将行政管理机构与机场分离,绝大多数机场移交地方管理。其本质要求是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行集团化管理,使企业做大做强;更好地调动地方建设和管理机场的积极性。从2001年开始准备,2004年基本完成。
企业重组
这次重组是按“企业自愿、政府引导、发挥集团优势”的原则进行的。在民航总局组织协调、企业通过沟通达成重组意向的基础上,国务院于2002年3月3日批准了民航体制改革方案。10月11日,原国家计委和民航总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民航企业改革重组大会,宣布三大航空集团和三大服务保障集团成立。吴邦国副总理作重要批示表示祝贺,并对确保安全、理顺关系和加强管理提出了要求。
三大航空集团公司是对原民航总局直属的9家航空企业进行了整合。其中,国航、中航和西南航归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东航、西北航和云南航归为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南航、北方航和新疆航归为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三大服务保障集团即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
实施这项改革,包含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也包括政资分开。重组后的集团公司,均与民航总局脱钩,移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这样做使民航政府机构更加超脱,更有利于面向全行业行使好政府职能。二是扩大企业规模,支持做大做强。规模网络化经营是航空公司突出特点,如此方能拓展市场空间,提高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三是按照专业化要求,促进服务保障集团的发展。
机场属地
这次改革的另一个重头戏,是对各省、区、市的民航单位,分别组建机场管理机构和航空安全监管办公室。除北京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和西藏机场外,机场统一移交地方管理。先在山东、湖南、青海三省进行了试点,然后全面铺开。
这样改革在地区管理局和省市区局层面,实现了政企分开。民航第二轮重大改革是集中在民航总局和地区管理局层面进行的。各地区管理局所在地以外的省、区、市民航单位,机场业务和行政管理职能仍在一起。因为省、区、市局归地区管理局管理,实际上管理局政企分开也没有完全到位。这次分离后,有利于机场的自主经营和自我发展。省、区、市安全监管办公室当时组建了26个,后来又有增加,现已改为安全监督管理局。
机场移交地方管理,是中央的一贯方针。在实施第二轮重大改革以来,随着地方对机场建设投资的增加逐步进行。这次全面改革机场管理体制,机场原则上交给地方。这样做既有利于行业管理部门强化政府职能,又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还有利于增强机场的活力。至于北京和西藏机场仍然由民航总局管理,主要考虑北京机场主要为首都功能服务,要打造大型航空枢纽;而西藏的高原机场则需要局方的大力支持。
民航这一轮重大改革,经历了刘剑锋、杨元元两任局长,高宏峰副局长分管改革工作、全面组织实施,其他副局长都有参与。记得我是在2003年11月26日参加了重庆民航的体制改革和机场移交。说来也巧,我1972年加入民航时就在重庆工作,这次能有机会见到原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童小平出席了交接仪式。回京时在飞机上恰好遇到王鸿举市长,他对这一改革也十分关心。但没过多久,重庆市又把机场卖给首都机场集团了。再到2016年9月,又通过市场化方式,全部交给重庆市。这都是在改革进程中发生的重大变化。
一主多元
我在撰写这次征文中所回顾的民航三轮重大改革,是指集中进行的、涉及全行业的深刻变革。但三个阶段在很多方面不能截然分开,如政企分开、转变职能、企业改组、机场属地化,以及相关配套改革,一直在持续进行。总体来看,随着改革的推进和不断深化,在航空企业和民用机场方面,都形成了“一主多元”的经济体制。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的“一主多元”,一是从所有制来看,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存的格局。航空公司普遍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很多成为上市公司。中央和地方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合办公司。在第三轮改革后成立的民营公司较多。二是从企业规模来看,形成了以大型企业集团为主导、与中小型航空公司并存的格局。通用航空则呈现出分散性,以小型企业居多。这是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民航机场的“一主多元”,从投资主体来看,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国家给予大力支持并有其他投资方参与的格局。从管理模式来看,以集团化管理为主,独立运作和委托管理并存。鉴于机场属于民航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社会公益性较强,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扶持政策。由于机场规模相差悬殊,大型机场完全实行企业化管理,相当数量的机场实际上没有真正按企业化来运作。机场管理体制还在不断完善,应该更好地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强化机场的管理和协同职能,促进平安、绿色、智慧、人文机场建设,加快打造航空枢纽,提升各类机场发展质量。
(作者为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现任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
来源/中国民航报
编辑/杨亚夫
转载请注明来自石家庄天鲲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标题:《改革开放40年:民航三轮重大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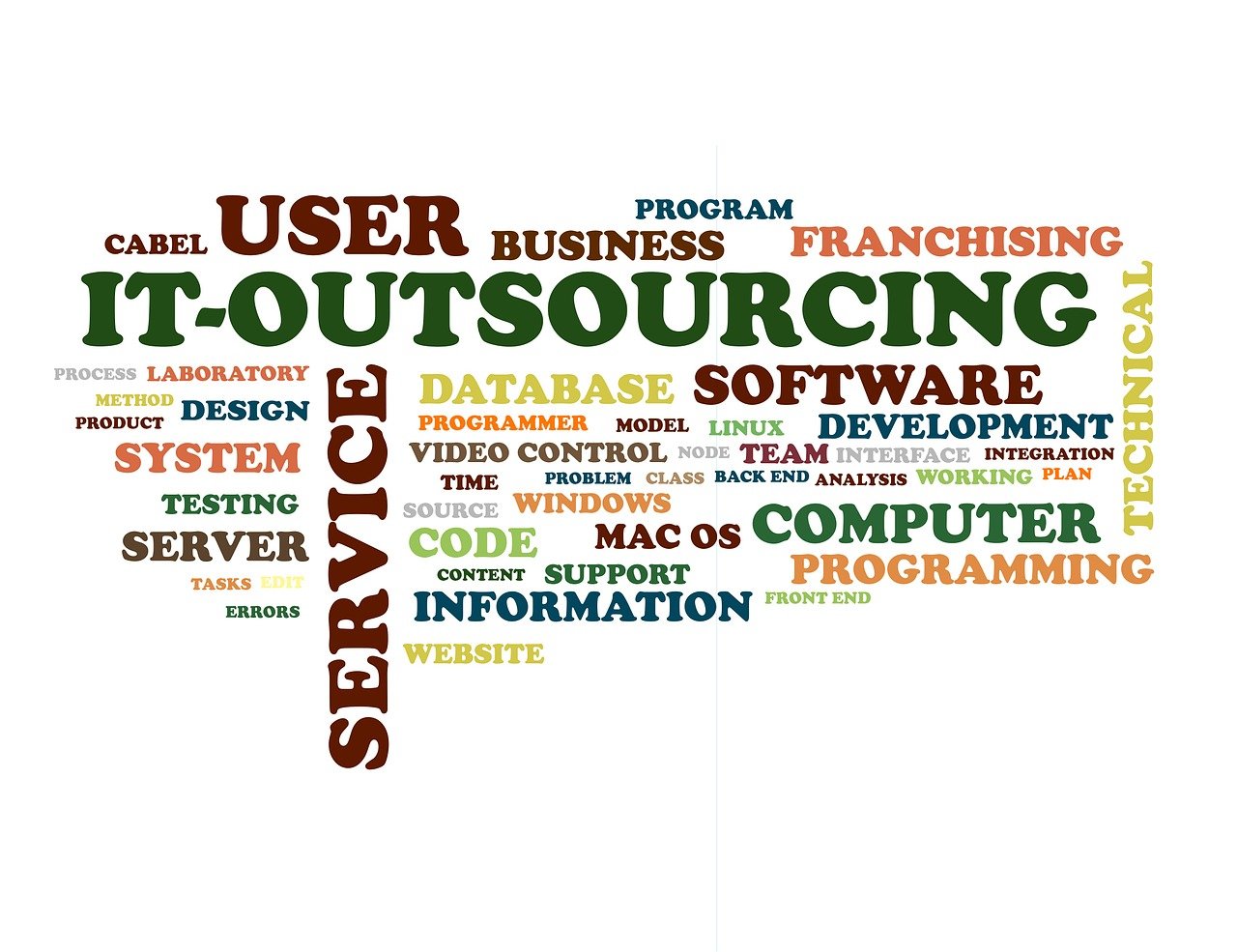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