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人生“善终”的知与行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王一方
在国家经济腾飞,国民生命质量、生活品质大大提升之际,人们便很自然地关注起死亡的品质与尊严来。因此,善终成为一项权利,一项福利。文明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能通过安宁和缓的医疗通道有尊严,少痛苦,愉悦地步入往生之途,善终也是一个社会的伦理共识,一场自我教育运动。通过新的生死观倡导,学习、交流生命善终的原则和技巧,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将通过相互关爱、呵护,帮助别人或得到别人的帮助而获得善终,这本《最后的拥抱》就是学习“善终”的绝好教本。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生轻死的民族,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常常被人们误读为“珍爱生命”的宣言。于是,时时幻想着颠覆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萌生长生不死(永生)的奢望,拒绝死亡也恐惧死亡,躲避死亡话题的讨论。君不见,产房内外,众亲拥簇,周到备至,相形之下,衰病之躯的临终时节,常常会失落孤寂,即使亲朋环绕,提供良好的躯体、医疗照顾,也无法使受伤的精神得到抚慰,将逝的灵魂得以安顿。因此,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以善终,但愿望在现实中常常落空。更多的是在无奈、无措中与亲人草草诀别,留下诸多无法补救的遗憾和撕裂性的别离哀伤。
在完整而丰富的生命历程中,一定少不了最后的送别、告别、道别的节目,也就是说,人的一生中总是会经历几次与亲人、朋友生死诀别的经验与体验,有限生命的境遇里,因为有生死惜别才会滋生对生命的无尽珍爱。这份珍爱也通常表现为对亲人的安宁照顾能力,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安宁护士,在医学生活化的当下,我们离不开医学的专业帮助,但死亡不仅与疾病(造成重要器官功能衰竭)有关,也与衰老(器官组织功能衰退、老化,最后归于停歇)有关,生离死别不只是一个医学与病魔抗争、完成躯体救助的过程,而是心灵的拯救与灵魂的救赎之旅,技术主义主导的现代医学尽管法力无穷,却无法抵达灵魂安抚的高度,也缺少临终时节(生命终末期)心理与心灵关爱、照顾与顺应的系统辅导。因此,抵达善终的送别是当代临床医学教学中最苍白的一课,无论医生、护士、家人都需要补上这一课。
人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善终与送别呢?《最后的拥抱》里,资深的安宁护士玛姬与帕特蕾茜亚用一系列鲜活的安宁护理与送别案例昭示我们,无痛苦,少折磨,不煎熬,死亡过程宁静、温馨,有尊严,有和解,那是最后一次体验亲情和智慧的仪式。生命长河里,亲情、友情是悠长的,但诀别只是一瞬间,一旦逝去,追悔莫及,永远也无法弥补。她们特别强调的是:生命诀别的过程是身心灵三位一体的,身-心-灵同步或者心-灵先于肉身迈向生命的终点,而不是躯体衰亡之时留下无限的心理遗憾,灵魂的无家可归。
这本书不是学理艰深的学术著作,也不是结构谨严的教科书,而是穿越个体丰富经历和体验的安宁护理札记,这种职业笔记传统由南丁格尔所开创,南丁格尔为我们留下的护理学著作就是那部不朽的《护理笔记》,这种文体轻松好读,适应性广,读者不限于医学生和专业人士,而是一部普适的人生教科书,它告诉每一个人,“善终”是你的需要,也是可以去虔心学习和感悟的日课。犹如莫里教授的《相约星期二》。书中每一个安宁送别的案例都不是简单的故事,而是包含着生死的观念与心态,谈话的方式与语境,沟通的技巧与仪式的叙事医学范本。
刚刚兴起的叙事医学将死亡从急救医学、ICU病房的技术氛围中解救出来,成为一个个生命之火从幽闪,返照,到最后熄灭的文学叙事,读完这些故事,你会觉得临死前的精神世界(作者命名为“临死觉知”)是那么阔达,以至于我们仅仅用病理学(心理与生理)的知识器皿来装盛是那样的局蹇,有长鞭窄室之困。徜徉在作者的故事里,你会觉得死亡叙事果真是一首诗,一首自我吟唱的诗,还是深情誦诗的美丽仪式,在这个庄严的仪式上,人们从容飞渡孤独、恐惧、沮丧、忧伤的心理峡谷,坦然接纳死期的降临,同时,尽情抒发生命最后的尊严,最后的爱,完成最后的拥抱。从此以后,肉身也可能“零落成灰无觅处”,“化作春泥更护花”,灵魂却腾入天国,自由飞翔,生命得以涅磐,得以重生。
书中死亡叙事的神来之笔是关于死亡历程的诸多“隐喻”,其中最常见的隐喻形式是“生命的远足”,死亡就是跨过一座桥,到远方去旅行,因此,临走之前要“找地图”,“找护照”,叨念着“旅程的艰辛”,亲人和友人要读懂这个隐喻,帮助将逝者勇敢上路,解脱他的最后牵挂;第二个隐喻是“穿越时空的灵异访问与重逢”,譬如见到早已逝去的前辈,多年不见的至交,这样的会面常常半虚半实,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如梦如痴,相谈甚欢,或许是过去的仇人与情敌,为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与这个世界和解,不留下仇恨、敌意与遗憾,这些相遇者都是将逝者未来生活的旅伴,与他们结伴而行,往生的路才不会寂寞;第三个隐喻是“谒神、遇仙或步入天国、仙境”,有宗教信仰的人会感觉到上帝、天使、真主、佛陀、观音的召见或邂逅,体验到天堂的胜景,或看到一束美丽的光,远眺一个美丽的地方,包含着平生积德行善的自我肯定,才会有遇仙或步入仙境的荣耀,有了这份荣耀,往生的路会平坦顺畅很多。
面对临终者形形色色的死亡叙事,玛姬与帕特蕾茜亚告诫我们,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家人与朋友,都必须服从叙事医学的“军规”,坚守故事语境与仪式,不能以科学(理性)语码来破译,恰恰要以文学意象(诗性)来建构,来领悟,不允许使用“这不过是临终幻觉”这分明是“药物过量反应”,“这是不可能的”类似的客观主义大棒去击碎那些美丽的诉说和体验。相反,要顺从将逝者的故事语境,辅以肢体的关爱(如抚摸,拥抱)讲故事延展下去,探寻下去,将隐喻解读得更丰满,更惬意。同时,记录下这些临死觉知,发掘出人类临终期(三个层面:民族文化独有意象,个人生活经历的独特意象,人类公共意象)的“思维地图”与“认知密码”,让死亡叙事的“剧本”更加丰富与丰满。
最后,要指出,这本书还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焊接”,那就是将临终关怀(针对将逝者)与哀伤关怀(针对将逝者家人)融为一体,真正打通了,逝者的家人只有在安宁护士的引导下积极参与身心灵三位一体的临终关怀,自然就会消除对逝者的撕裂性哀伤,转而进入绵绵不尽的追思和怀想。或者有望成为优秀的安宁义工与志工。因为中文里“舒”字由“舍”和“予”组合而成,仓颉造字法提示我们:只有舍得给予,才会赢得生命中最大的舒坦。
给临终者以“最后的拥抱”
——代序言
中国抗癌协会 副秘书长兼康复部部长
北京军区总医院 主任医师 教授 刘端祺
这是一本讲述死亡的故事集。我们从作者娓娓道来的60位逝者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临终前的种种体验看到:不管人生是多么精彩还是多么坎坷不堪,死亡可以同样厚重而庄严。
本书寓教于情,可读性很强,不少地方引人入胜,使你在关心主人公命运的同时,不禁掩卷沉思,走进作者的世界,随作者一起思考人生的价值、死亡的意义。
作者Maggie Callanan 和Patricia Kelley是从事临终关怀的资深护士,她们面对着一个个境况不同的终末期病人,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仁心大爱。出于对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患者的尊重和同情,她们千方百计地了解患者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以及物质和灵性的需求,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克服各种困难,解决患者的身心困顿,给患者以最适于他或她个人情况的恰当处置。正如作者所说:“我的职责是尽量让病患感到安适,并非只是生理上的舒服”,“送人临终和迎接新生命一样,都可以是全家人分享正面意义体验的机会,并非只有悲伤、痛苦和失落。”她们作者既是医务工作者,又是心理学工作者,还是社会工作者和虔诚的教徒。她们在帮助患者辞世的实践中贯彻始终的“共情”、“同理”和“全人服务”的职业精神,既是传统意义上医学的回归,更体现了医疗卫生界和思想界对医学本源和生命本质的时代思考。
惧怕死亡,不愿直面死亡,因而有意无意地回避死亡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社会维持正常运转并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但同时,这也造成了古今中外在实施临终照护时,在观念和心理方面的共同障碍。社会关注度的不足,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人群理念的差异,医疗、经济水平的限制及社会、文化等无形因素,都在影响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和医学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骄人成就相比,做为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临终关怀事业,直至20世纪下半叶还少有专业人士问津,理论研究固然缺位,临床实践也基本没有到位。致使临终关怀这个自人类诞生即存在的“古老问题”,至今还是一门在不断探索中的“新兴学科”。
不具备临终关怀专门知识的医生面对即将不治的患者及其充满悲戚的亲友,往往“既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只得把一般的临床治疗常规和护理模式“移植”到临终处置,在一系列看似“周到”的医患沟通和貌似“严谨”的技术操作中,使死亡来临时的诸如维持酸碱平衡、呼吸机运转、生命指证的监测、心脏按压、种种插管注射等,都成了“表演”和“仪式”,成了冰冷的、程序化的人生结局。面对医院复杂的抢救器械和亲人身上连通的各种“救命”管道,人们往往认为,患者的生死掌控在医生手中的电源插销或护士手中的药针里。显然,这是由于以技术至上为特征的科学主义盛行,背离了人文理念的过度医疗所造成的对“临终关怀”的严重误解。它把一个本应充满凝重悲情,温馨而又私密的场合变成了技术“秀场”,使逝者成了医院“规范作业流水线上的物件”,剥夺了生者与弥留者亲情道别的最后权力。
值得欣慰的是,本书的作者摈弃了已被沿袭多年且已固化的“抢救”模式,以完全个性化、人性化的思路,用全新的理念协助临终者及其亲友共同设计并完成了符合逝者生前意愿的“人生落幕式”。在书中,我们看不到医护向病患及其家属刻板的“交代病情”,听不到“生命不息抢救不止”的嘱托,更没有手术室里“金属与肉体”的碰撞。作者并不讳言她们在为患者服务过程中留下的诸多遗憾,但给临终者以“最后的拥抱”的强烈愿望,总是促使她们无微不至地给临终者送去人间最后的温暖。
最近,境内外学术界(临终关怀、心理、哲学、生理、宗教等)对实施“灵性照顾”多有关注,提出:医护人员要像重视患者身体的症状和心理状况一样,随时掌握患者的灵性动态和需求,关注患者的灵性困扰,有的放矢地实行灵性照顾。
灵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个人体验。临终状态时的灵性是指:面对即将不久于人世的现实,在人际交往、社会关系方面所产生的对历史和未来的一种难以言传的心绪历程。它是介于生理和心理之间的一种身心之外因人而异的体验,可以是幽怨、恐惧、焦虑、烦躁、愤怒、忧郁和孤独等负面作用力的混合体,也可以在正面力量引导下衍化为内心和谐、处世积极、恬淡平静、了无牵挂、直面死亡,摆脱了身心痛苦的一种人生境界。
世俗注重生、注重肉身,宗教注重死、注重灵性。但这并不妨碍没有宗教情结,信仰无神论的读者对灵性问题的探讨。灵性照顾已成为临终关怀不可或缺的内容。近来,大陆学者展开了对灵性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临终时灵性照顾的研究,本书的一些做法和观点可资借鉴。
我们大可不必理会贯穿于本书的宗教理念和对灵异事件的解释,也不必介意灵性是否仍然属于心理学范畴的讨论。本书需要关注并理解的内核和精髓是:作者在以慈悲为怀的临终关怀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人性光辉。
临终是生命的一个自然阶段,死亡不能被简单地看成是医学的失败。只要有死亡,就需要临终关怀。它是基于人类现有认知水平的一种顺势而为的积极的医疗行为,需要综合性的专业技术支撑,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是医学进步的重要表现,而非医学的无奈之举;它理性舍弃对患者无益甚至有害的过度治疗,代之以符合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最大利益的适度治疗和护理,使逝者临终前享受到先进的医疗理念和技术服务,离世时身无痛苦,心无牵挂,灵无恐惧,社会上有尊严。这种有厚重文化底蕴和现代科技内涵的临终关怀,可以使逝者感到自己“死得其所,死而无憾”,是人生的“完满句号”。
青年时期,我曾在甘肃南部多民族地区工作多年,经常服务于临终患者。在弥漫着超度逝者灵魂诵经声的藏传佛教拉卜楞寺旁,目睹远处穆斯林们静穆的葬礼,联想汉族群众丧亲后的呼天呛地,我惊异地看到,不同民族乃至同一民族的不同群体,对生命的逝去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在受到震撼的同时,也使当时还年轻的我,开始对生命有一种别样的敬畏、思考与尊重。
医生这个职业使我们比大多数人都更多地接触死亡。死亡是一种伟大的平等;死亡也是一个伟大的教师。正是由于死亡的存在和不断的“教育”、“提醒”,才使我们感到生命的可贵和人生的价值,充分地享受人生,珍惜当今的分分秒秒,珍惜自己与家人、友人乃至素未平生的陌生人相处的宝贵时光;同时,敢于直面死亡,思考死亡,理解死亡。医务人员应当做“阅读死亡”的有心人,在阅读别人的死亡中不断升华自己。
本书可以作为生命教育、辞世教育的读本,供从事临终关怀事业的同道们常备于案头;建议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和护士朋友也应该阅读这本书,相信会从中受到多方面的启迪。非医学专业的朋友们如浏览本书,可能有助于树立起这样的信念——既然死亡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生终点,当它即将来临时,我们不仿心境淡定,从容面对,优雅地转身,让死亡和降生同样神圣、同样美丽。
本书的英文版简介中说:通过阅读本书,“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那些即将逝去的人们以近乎奇迹般的方式传达着他们的所需,分享着他们的感受,甚至编排着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也会发现那些即将逝去的人们留给生者的礼物——智慧、信念和爱。”这是对本书的英文原名《Final Gifts》的很好的诠释。
让我们珍视并研究这份“最后的礼物”,并给临终者以“最后的拥抱”。
2012年10月
转载请注明来自石家庄天鲲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标题:《最后的拥抱(了解人生终点时的渴望和需求,让生命的离去更加从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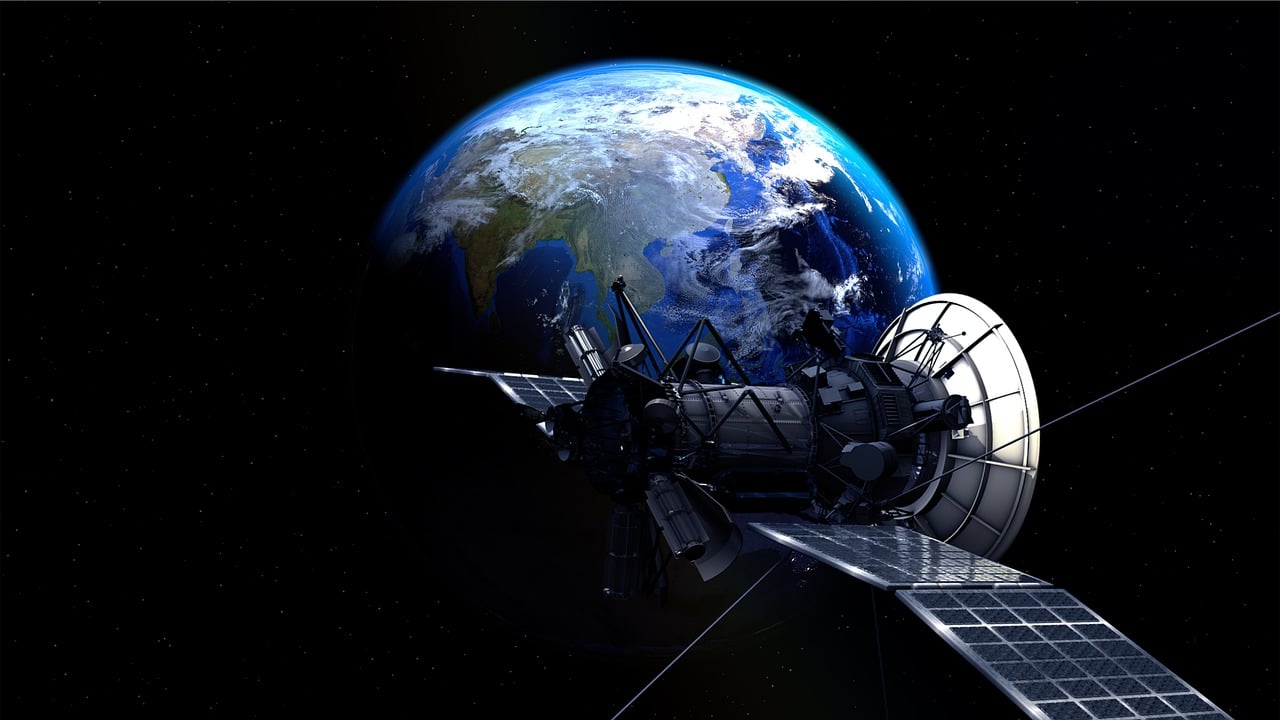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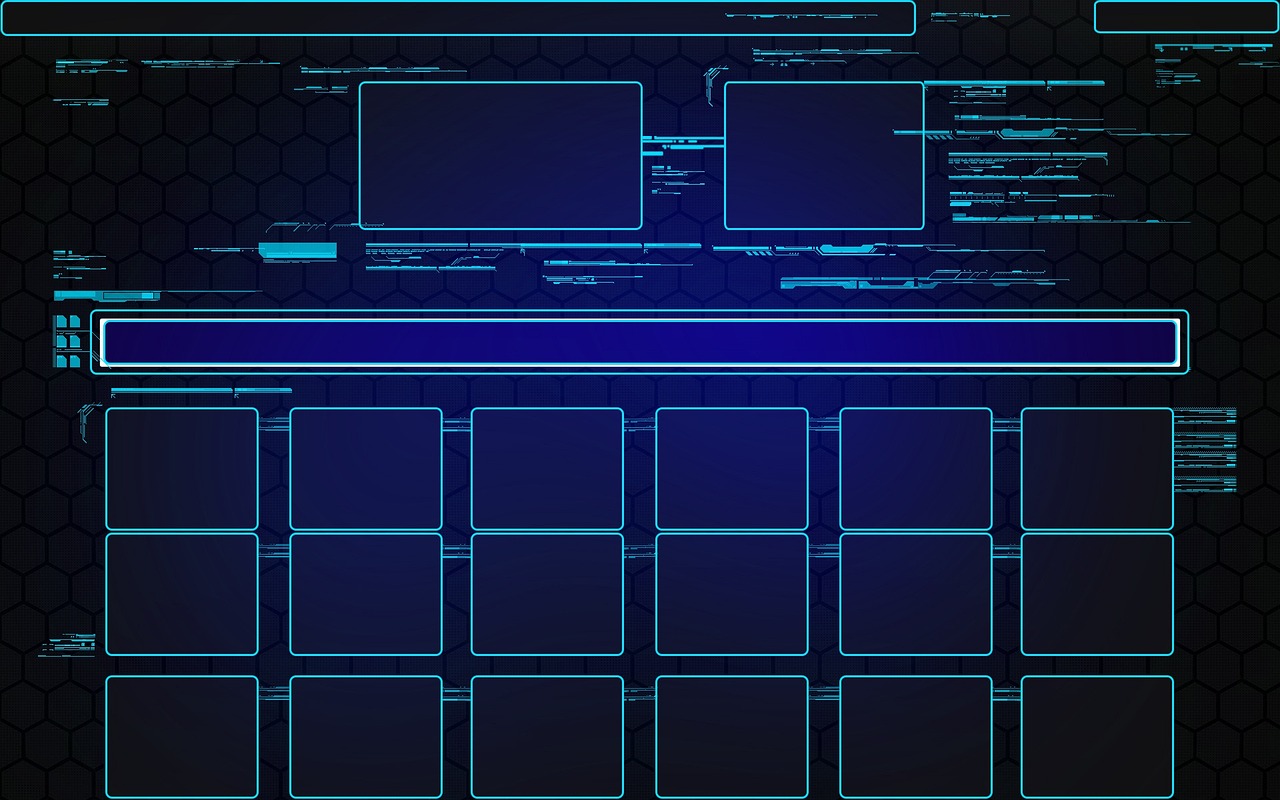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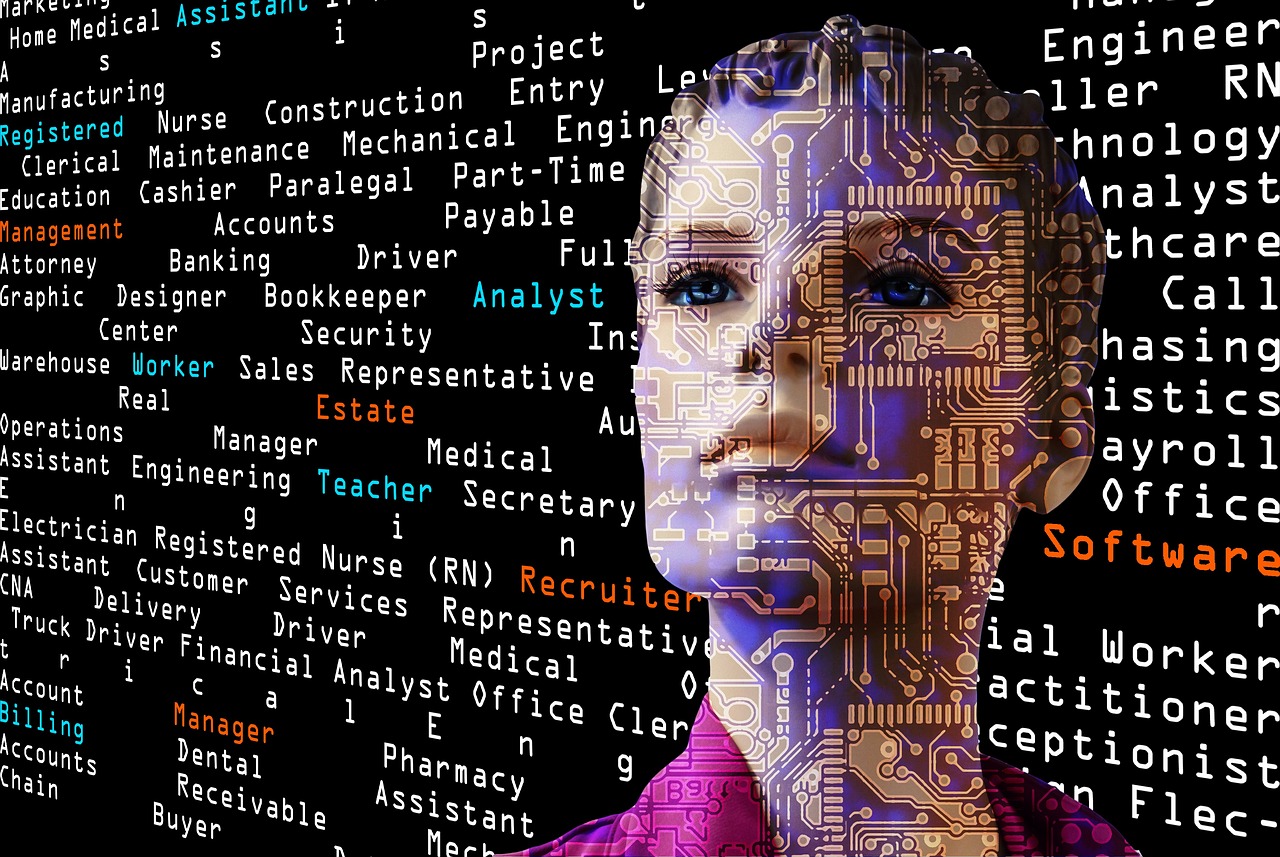





 京ICP备16045314号-1
京ICP备16045314号-1  京ICP备16045314号-1
京ICP备16045314号-1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