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河
《天工开物》几乎所有的呈现形态都与“剧”的本质要求关系不大。它就是一台带着舞味儿的“秀”。情怀不在,敬畏不在,力量不在,疯长的只有刺激,只有声、光、影、电、形带来的感官冲动,以历史、人文、题材的名头,行轻率浮皮之事,彰秀场浮华之姿,越繁茂,越悲哀!
由陆川执导、江西文演集团与北京舞蹈学院共同出品的《天工开物》,除了节目册上明确印着“舞剧”外,这部作品宣传用的是“舞台剧”,演出现场字幕用的是“跨界融合作品”,我看着就挺想乐。这到底是个什么作品呢? 看完全剧,我想大体可以这么称呼它:舞味儿“秀”。
01.有“舞”没“剧”
循着节目册“舞剧”这个称呼来分析,其实现今最常见的,是有“剧”没“舞”。这当中关系到本体规律要求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文本构架完成之后,舞剧的创作者、编导们,缺少用舞蹈语汇进行准确表达的能力,更缺少基于舞蹈本体的艺术表现认知。因此,很多作品传递出的,是故事结构下的肢体还原再现,可能是哑剧,也可能是单调重复的动作表达,谈不上语汇的合理延展与发展,更谈不上舞剧舞蹈这一艺术审美的张力与魅力。这类作品,现在能看到太多太多,可以说,大部分如此。
但这个剧恰恰相反,有“舞”没“剧”。《天工开物》是一部了不起的大书,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古代中国,格物致知,再以知致政、致仕,这是常态常理。明代宋应星屡试不第,转向格物穷理的非功利化纯粹,这跟游历山川、书写游记的徐霞客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文化史上的此种异类存在,是很值得玩味的。宋应星与《天工开物》,没有那么多的外在戏剧性,但其所透出的科学精神和自然哲学,用舞剧做诗化表达,极有可能是适配的、高级的、迷人的。它大概就应该是那个气质、体质。
然而并没有。它没“戏”。四个部分,大致均衡,一是“赶考”,就是纯赶考;二是“应考”,就是考试加没考上;三是“著书”,把《天》书中所列工艺择要再现;四是“山河”,是段莫名其妙的讲述,大致说成书于乱世吧,内容与人、与成书,关系都不大。 严密的叙事逻辑自然是谈不上的,叙事结构也无从说起,所有精神层面的表现,更未触碰。写人吧,故事可以按在所有应试不爽者的头上;写书吧,除了剧中人拿支笔在空中凌乱地比划外,没见与写其他书的作品有什么区别。最多不过多了些浮皮潦草的工艺场景,那些“皮”,既光鲜,又苍白,它们都不在“戏”里。
“舞”是有的,而且很多。出品方其实很明白,他们知道主创对舞蹈舞剧的认知水平。于是缺哪儿便恶补哪儿。他们拉来了北京舞蹈学院做联合,把北舞青年舞团拉上了舞台,又一股脑儿地将北舞的教学实践积累堆上了舞台。丰富的语汇、超正的古典舞范儿加上纯熟的舞台能力,舞,必定是有得看的。
只是,只能就着舞段自身说,不能考虑它们的戏剧功能。仔细看下来,这个舞台上,更像是北舞的教学成果展示。片段化、小品化的若干舞段一个接着一个来,训练的程式化几乎未脱,呈现的不过是贴了些动作标签。比如“乃服”,就是弄了些缫丝纺纱的动作;“陶埏”,就是陶瓷工艺中打坯的动作;至于“赶考”“应考”,也都是你想的那些,没错,就是所有普通观众所能想到的那些。舞剧舞台上程式化了的东西,终是逃脱不了单一重复,要想往戏剧表达深入一步,那也是不可能的。至此,我不再分辨再现、表现等可能会更深层次哪怕一点点的命题,因为 几乎所有的呈现形态都与“剧”的本质要求,关系不大。它就是一台带着舞味儿的“秀”。
02.缺乏起码的敬畏
这个作品做成这样,并不意外。我相信每个领域都会有天才的艺术家,但不相信有通吃天下者。陆川有才华,创作过很好的电影作品,万万没想到,他竟敢染指舞剧。对专业人士,总有句劝慰:内行不要跟外行啰嗦,说不清;而对于业余者,也有句规劝:轻易别跟专业人员比高低,会被降维打击。现在倒好, 业余人士、初级入门者都算不上的外行,登堂入室,操局控盘,堂而皇之地把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艺术行为,做成了“儿戏”。
艺术需要敬畏,舞台需要敬畏,在这两个字面前,勇气毫不可嘉,甚至一文不值。舞剧艺术,职业编导们大量探索实践,才有可能摸到门边,这当中的极少数因其艺术理想、人文素养、天才领悟、语汇储备、创作能力等,在某个领域或者题材表达上的契合,才成就舞台呈现的光彩和舞剧审美的光泽。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经年的失败磨炼与反复求索,是不可能获得有效抵达的路径的。至少,舞剧很难。舞蹈这个依靠肢体表达的艺术,欣赏谁都可以,创作却有极高的门槛,要想形成本体审美的效力,构成统一与纯粹的、充满艺术张力的系统性舞剧作品,谈何容易!要不然,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有“剧”没“舞”的作品了。
有人说,陆川只是总导演,你没看后头还缀着一位总编导么?总导演出思想,总编导和她(他)下面的小编导们出技术,完成呈现。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很多舞剧也都是这么干的。但实际上,挂着总导演、编剧的陆川,又给出了何种思想呢?即便有,又如何落到舞蹈表现的外化与呈现呢?他大概想不到这么多,或者说,这是他无法解决的问题。这里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度二度关系的事情。冒昧揣测,更大的可能性是,包工头儿,接了这活儿,分包给下一环节罢了。至于敬畏,在票子而前,大概才是一文不值的吧。
现状如此,现实如此,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别人无法置喙。在舞剧创作看起来繁荣、实践越来越浅层化、感官化的今天,大家似乎都忘记了舞剧是复杂的、舞剧创作是痛苦的这个事情,从编到演、到观者,终于把艺术平顺地过渡成了消遣, 情怀不在,敬畏不在,力量不在,疯长的只有刺激,只有声、光、影、电、形带来的感官冲动,以历史、人文、题材的名头,行轻率浮皮之事,彰秀场浮华之姿,越繁茂,越悲哀!
即便是作为电影导演的陆川,在多媒体视觉的擅长领域,又给这个作品增厚了什么呢?大屏幕上那个“大手”和“大脚”的动画特效?定制灯光带来的那点梦幻场景?我只觉得无聊。敬畏这个事,不轻易染指是一方面,还包括对既有艺术规律的尊崇和吸纳。比如,艺术要表现人;比如,要通过典型而特殊的艺术形象来表现精神特质;比如,心理情感要通过特定的本体语汇实现外化,等等。这个剧似乎连这些最基本的要求也谈不上。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跨界”也成了一个艺术标准了。这样的跨法,也不怕扯出毛病。
03.匪夷所思的文化操作
这几年,舞台艺术投资,大手笔是真不少。据说《天工开物》这个剧花费在三千万以上,上多少,不得而知。越来越搞不清楚,做一部舞台作品怎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名家大腕?光影特效?实不得而知。钱多钱少是不能一概而论,有些舞台类型也确实一分钱一分货。但很多地方本来经费就有限,没有实力去做体量大、花钱多的歌剧舞剧项目,优势也不足,也不贴合自身文化定位,做出来不伦不类,真不知何苦来哉?
有的地方、有的出品单位,在这方面的发挥几乎达到极致,这几年动辄几千万一部的舞台作品太多太多。再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说句难听的, 这些主创们、导演们、主演们,以及合作的院团长们,是不是将这种舞台当成试验田、当成取款机?在上面“耕耘”的,什么奇葩都有,背后的东西,也当真值得细品。
商业投资搞个什么“大型”、弄个“秀”啥的,不管文化上能否留下一笔,把钱挣回来,好歹是个交待。然而,这样巨额资金投入制作的作品,即便能够走得远些、能够拼尽力量去多演些,也很难回本。更何况,这么大的舞台、这么多的人,实在很难走得出去,走得很远。劳民伤财,资源浪费之后,终是一地鸡毛。 一两个浮夸的东西,真够得上做十部八部甚至更多紧贴当地文化特色的、彰显艺术力度的作品的开销了。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嗷嗷待哺的基层戏曲院团,难道不会更加悲凉!
更奇葩的是,这个作品从主创到主演,没有一个是当地人!节目册上还赫然印着吉林市歌舞团,这么看,相当一部分群舞演员也是外来的。这属于典型的演了这顿不知下顿在哪里,能不能再演:成本是一方面,外来队伍档期也是个未知数。这样匪夷所思的操作,最终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又能真正留下什么呢?
发展文化,总不能逢人只能解释“我也是一片好心”吧。(常河)
转载请注明来自石家庄天鲲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标题:《舞味儿“秀”——陆川舞剧《天工开物》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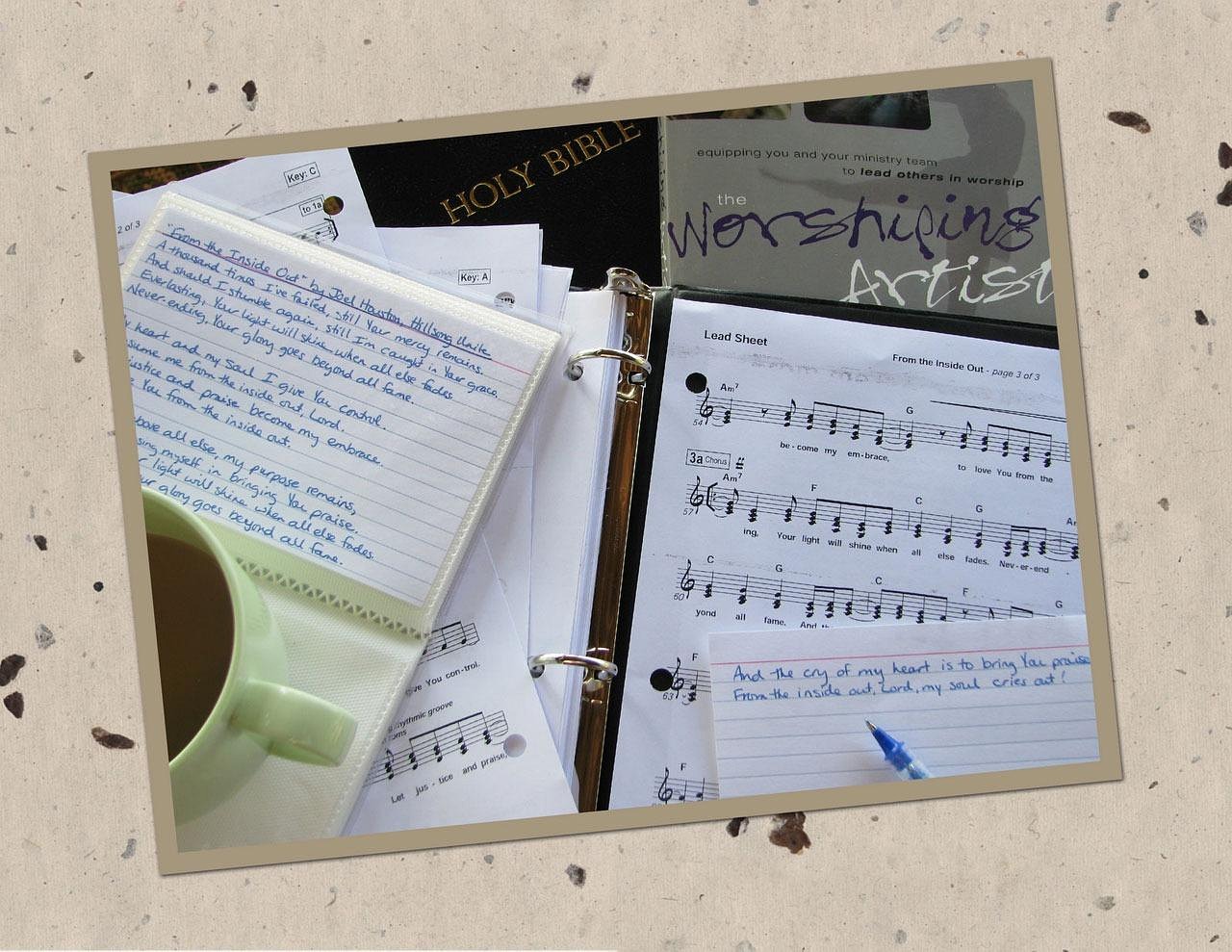





 京ICP备16045314号-1
京ICP备16045314号-1  京ICP备16045314号-1
京ICP备16045314号-1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